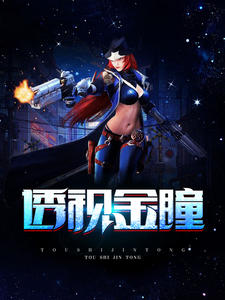保安大叔罵罵咧咧的跑出崗亭,似乎是去攆一個開黑救護車的。
顧漣漪朝門外發廣宣品的奶奶要了一頂帽子,黑色的,印着『夕陽俏旅行社』,質感很low,優點是大小很合適。
她將帽檐往下一壓,悄悄跟在後面。
跟了足有兩條街,年輕夫妻拐進一條小巷子。
那裡停着一輛銀色的雙排座帶斗小貨車,車身上的灰很厚,不知被哪個調皮的孩子畫了個豬頭。
哐。
丈夫將蛇皮袋扔進後面的斗里,濺起大團灰塵,妻子抱着襁褓坐到副駕。
見男人輕手利腳的進了駕駛室,躲在牆邊的顧漣漪伏低身子迅速靠近,悄悄翻身上斗。
她全程沒有發出明顯響動,動作敏捷,像一隻靈巧的貓,
許是女人特有的第六感使然,副駕處的妻子忽然回身,顧漣漪一驚,嗖的趴下身子。
妻子透過後窗掃了一眼空無一物的街道,她撇撇嘴,將懷裡的襁褓放到後排座椅上。
現在差不多5點,五月的金城,天色依然大亮。
巷弄里的路挺顛簸。
顧漣漪抬頭看地形,貨車一旦開到大馬路上,趴臥在後面的她一定會被旁人發現。
道具有限,她忍着膈應,扯過身邊一塊看不出顏色的大氈子,揚臂一扯,蓋在身上。
氈子布很大,也相當髒,兜頭蓋下的瞬間,灰塵和怪味齊齊撲到她臉上。
她嫌惡的皺緊眉頭,小心翼翼的扒開一個小口子,讓自己能呼吸一點新鮮空氣。
不一會兒,有嗚咽聲傳來,輕輕的,低低的,幾不可聞,但顧漣漪聽到了,那是嬰兒的細弱哭聲。
她把氈子布扒開一點兒仔細聽,哭聲逐漸變大,約莫一分鐘後,終於變成清晰可辨的啼哭。
「媽的,怎麼醒了?!不是說給一次藥至少能睡十個小時?」屬於男人的粗嘎聲音,夾雜在廉價發動機的噪音中。
「你問我,我特麼問誰!」
女人話音尖利,嬰兒受到驚嚇,伴隨着一陣劇烈的嗆咳,哭得聲嘶力竭。
「醒就醒了吧,你是女的,你想辦法讓她閉嘴。」
「我是女的又怎麼樣,我特麼又沒生過,誰知道怎麼弄……誒,你說她是不是餓了?」
男人不耐煩的答道:「那你就給她餵點。」
「喂喂喂,擱什麼餵?你有奶呀?等會碰見小超市,你下車去買一袋牛奶,買兩塊錢一袋那種就行,別買貴了啊。」
男人聲音忽然黏糊起來,「這麼摳呢,那乾脆別買,你衣服一拉,讓她吃唄。」
「艹!調戲老娘,你當我是奶牛,想吃就有?」
「是不是奶牛不知道,要不我先試試?來,自己把衣服拉起來,我還開車呢,騰不出手。」
「滾……你看點路,你想死我還沒活夠。」
一句句不堪的話強鑽進耳里,顧漣漪漂亮的眸子漸漸黑沉,冷氣縈繞周身。
她緩緩起身,透過後窗往裡看。
髒亂的后座上,粉色的包巾一大半散落在地上。
女嬰身上的衣服很髒,拳頭緊攥着,臉色漲紅,嘴唇已呈現哭到缺氧的青紫。
光光的額頭上,是一個鵪鶉蛋大小的鼓包,絳紫色,脹得發亮,周圍隱約一圈兒黃。
這哪是什麼血管瘤,明明是被人反覆對着一個地方敲,硬敲出來的包!
顧漣漪看着這畫面,戾氣驟生。
……
一個小時前,治安崗亭里。
「叔叔,火氣這麼大對身體不好,請您喝罐涼茶,咱們聊聊。」
「跟我個老頭子有什麼可聊的?」
顧漣漪直奔主題,「叔叔,那對兒夫妻是不是有問題?」
保安大叔看了她一眼,重重的哼了一聲,恨恨道:
「一群沒腦子的,那麼大歲數都白活了,還趕不上你個黃毛丫頭眼尖!
我當保安十幾年了,什麼牛鬼蛇神沒見過?我一眼就看出他們不是好東西。
那兩個人在這裡三天了,你說說,誰家孩子有病不進去醫院看病,每天就這麼抱着?
在門口一坐就是大半天,賣慘裝窮,說他們沒鬼,我把腦袋摘下來給你。」
「咳,您別激動,您去看過那孩子嗎?真有病嗎?」
保安擺擺手,粗聲粗氣的說道:「我倒是想看,他們捂得嚴嚴實實不讓我看,倒是那些給錢的傻子看過的,說是腦袋上好大的一個包!
這就更有問題了,孩子病這麼重,就算賣房子賣地也要趕快治,賣口香糖?賣到猴年馬月去!還不是要裝可憐,騙這些傻子捐錢?!就那個破箱子,看見沒有,一天下來起碼裝滿兩三次的,至少要大幾千塊!」
顧漣漪看着暴躁的保安大叔,一時不知道說啥好。
大叔智商邏輯雙雙在線,心思縝密,觀察入微,就是這情商……
保安大叔又說:「我看這孩子要嘛就不是自己的,要嘛就是孩子本身是傻的,一聲不吭就是睡覺,哼,倒是乖得很。」
顧漣漪眉頭皺緊:「您說,孩子很乖,就是睡覺?」
「是啊,就是睡覺,不哭不鬧。」